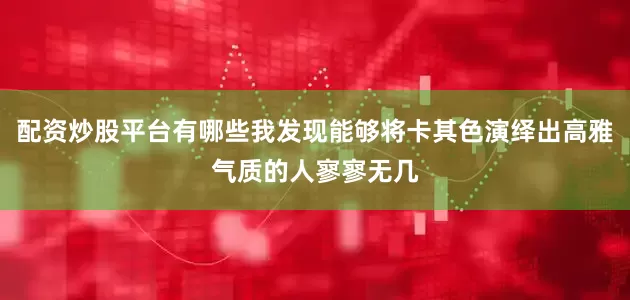2025年8月15日,一则人事任命悄然挂上官网,吉训明院士出任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院校长。
这是一个相对陌生的 名字。
但在经历了数月的舆论风暴后, 这个名字的分量,已截然不同。此刻接掌协和,意味着什么,外界正拭目以待。
而关于协和的记忆深处,住着一位几乎每个中国人都认识的前院长,顾方舟。 他的另一个名字是:
糖丸爷爷。
他为一代协和领导者确立了坐标:他们的使命,是为这个国家的人民解决最棘手的健康难题。

然而,当历史的车轮驶入21世纪,这一定位开始发生微妙而深刻的偏移。
他之后的继任者们,与公众命运的缠绕,不再仅仅是作为危机的解决者。
他们本人,以及他们所代表的体系,开始越来越多地成为问题的一部分。
1
要理解这一切,需要将时钟拨回到20世纪50年代末。
彼时,一种名为脊髓灰质炎的病毒,正在中国的儿童中间肆虐,它更为人熟知的名字是:
小儿麻痹症。
疫情汹涌,无数家庭坠入恐慌与绝望。
时任中国医学科学院院长的病毒学家顾方舟,和他的同代人一样,面临着一个新生国家百废待兴、一穷二白的现实。
摆在他面前的,是一个艰难的战略抉择。
当时,国际上有两条疫苗技术路线。
美国科学家索尔克(Jonas Salk)发明的死疫苗,安全性高,但工艺复杂、价格昂贵,且需要注射,对于当时的中国而言,无论是生产能力还是接种成本,都难以承受。

口服疫苗的小孩
另一条路,是苏联科学家萨宾(Albert Sabin)偏向的活疫苗,它使用经过减毒处理的活病毒,药效更强、成本极低,且可以口服,但其安全性在当时仍存在巨大争议。
顾方舟做出了判断:
中国只能走活疫苗这条路。
他带领团队,在云南昆明一个由山洞改造的简陋实验室里,开启了这场豪赌。
经过无数次实验,1960年底,他们成功研制出了中国自己的脊髓灰质炎减毒活疫苗。
真正的考验刚刚开始。
疫苗进入临床试验阶段,其对人体的安全性,尤其是对儿童的安全性,仍然是一个巨大的未知数。
在那个没有严谨伦理审查流程的年代,科学家们只能用最原始、也最决绝的方式来验证自己的成果。
顾方舟和他的同事 们 率先服用了那杯悬浮着活病毒的疫苗溶液。
据称,顾方舟自己一个人就在一个晚上服用了:
100份疫苗。
但这还不够。
成人试验的成功,并不能完全代表它对免疫系统尚未发育完全的婴儿同样安全。
为了拿到第一手数据,顾方舟做出了一个在今天看来无法想象,也绝无可能被批准的决定:
他给刚满月的儿子,喂下了疫苗溶液。
我们今天已很难去评判那个选择。
那是一条横亘在科学伦理与公共利益之间的钢丝,是一位科学家在极端压力下,将自己的骨肉置于天平之上的一次献祭。

幸运的是,他的儿子安然无恙。
随后,他的同事们也纷纷效仿,给自己的孩子服用了疫苗。
这颗后来被亿万中国儿童含在口中的糖丸,其最初的甜味里,混合着那个时代特有的、令人百感交集的复杂况味。
2
在顾方舟的时代,协和还拥有另一座精神上的堡垒。他的名字叫黄家驷。

如果说顾方舟的战场在实验室,敌人是凶猛的病毒,那么黄家驷的战场则在会议室和时代的洪流中,他要对抗的,是无形的:
意识形态风暴。
黄家驷本人就是协和精神的完美产物。
1933年,他从协和医学院获得博士学位,后赴美深造,成为世界顶级的胸外科专家。

他的人生轨迹,完美诠释了协和“高进、优教、严出”的精英培养理念。
而他一生最重要的使命,就是守护这个理念的载体:
协和的八年制医学教育。
1949年后,国家对医疗人员的迫切需求,催生了以缩短学制、注重实用为导向的全国性政策。
协和源自美国的八年制,耗时长、投入大,在那个强调多快好省的年代,显得格格不入,甚至被批判为脱离群众的:
资产阶级教育。
压力是巨大的。
1957年,协和八年制被迫停办。
但黄家驷和时任协和医院院长的张孝骞(后来前往了湘雅医院)等人没有放弃。
他们积极奔走,向中央陈情,力陈为国家培养顶尖医学科研人才的不可或缺性。
仅仅两年后,奇迹发生了。
1959年,以原协和为基础的八年制中国医科大学得以恢复,黄家驷亲任校长。这是他为协和筑起的第一道防线。
真正的风暴在1966年降临。
文革期间,协和所代表的一切精英主义思想都成为被攻击的靶心,学校再次被迫停办,黄家驷本人也受到残酷迫害,和张孝骞一样被关进牛棚。

在那种极端环境下,公开的对抗无异于自取灭亡。
但黄家驷的抵抗转向了内部,转向了更为坚韧的方式。他与流散各地的学生保持联系,为他们寄去书籍,鼓励他们不要放弃学业。
据其学生回忆,他甚至曾当面向周恩来总理陈述,为那些学业中断的学生争取回炉再造的机会。
他守护的,是协和的火种。
风暴过后的1977年,在一次决定中国科教事业命运的座谈会上,黄家驷再次站了出来。
他与包括张孝骞在内的其他资深科学家一道,紧急呼吁挽救被耽误的一代学子,提议从文革前入学的高年级学生中选拔优秀者继续深造。
他的呼吁,成为那个冰封时代的一声惊雷。
1979年,国务院正式批准:
恢复协和医学院及其八年制。
黄家驷守护的,是一种在当时的主流政策之外的例外。
他像一座堡垒,抵御着外部风暴的侵蚀,确保了中国最顶尖医学人才的培养链条,在一次次政治浩劫的冲击下,没有彻底断裂。
3
历史的车轮滚入21世纪,外部的惊涛骇浪渐渐平息。
协和的院长席位上,迎来了一批新的面孔。
从免疫学家巴德年,到分子生物学家刘德培,再到肿瘤学家曾益新,他们是各自领域的顶尖科学家,是典型的:
技术官僚。
在他们任内,协和稳步地与国际科研体系接轨,发表的论文数量与日俱增,获得的国家级奖项也愈加丰厚。
在公众视野里,这是一个相对平静的时期。协和似乎正沿着一条现代化、专业化的轨道平稳运行。
然而,也正是在这片看似风平浪静的水面之下,新的挑战开始酝酿。
威胁不再来自外部清晰的敌人,而是源于时代洪流的冲刷下,肌体内部逐渐显现的裂痕与病变。
王辰院士,正是那位 试图以大刀阔斧的行动,重塑这所百年老院未来走向 的关键人物。
2020年初,新冠疫情突袭武汉,医疗系统濒临崩溃。
时任协和院校长王辰院士,基于对武汉疫情形势的判断,率先提出:
建立方舱医院。
这一举措,被宣称旨在快速隔离大量轻症患者,切断社区传播链,为定点医院集中资源救治重症患者创造条件。
该建议被迅速采纳,成为当时中国应对大规模感染的关键决策之一。
但其在隔离环境下的管理、交叉感染风险以及对患者心理的影响,也使其在国内外饱受争议。
这位出生于山东德州的呼吸病学专家,将他的 改革魄力应用到协和自身的教育体系时,却最终暴露出深层的内部病灶。
他力推的4+4临床医学专业培养模式,是他为协和设计的未来。
他曾系统阐述过这项改革的宏大愿景:
纳多学科素养者从医、纳天下贤才从医、纳爱医者从医。
该模式旨在招收已在国内外高水平大学完成四年本科学业的非医学专业优秀毕业生,直接攻读医学博士,目标是培养具有宽厚人文与科学基础的复合型医学领袖。
这是一个雄心勃勃的精英主义理想,试图为中国医学专业教育开辟一条全新的:
超越高考分数评价的道路。
但这条新路,仅仅五年后,就被证明是一条可以被特权轻易打通的捷径。
2025年春天,协和4+4试点班毕业生董某某被曝出系统性造假。
国家卫健委与教育部的联合调查通报,如一份精准的病理报告。
董某某申请入学时,本科成绩单中4门课程共计16个学分为伪造,由其担任北京科技大学处长的姑姑一手操办。
其博士学位论文与同年毕业的一名硕士生论文高度雷同,构成严重抄袭,同样由其姑姑向导师打招呼获得。在临床实习期间,她作为实习医生,违规参与了需要主治医师级别才能操作的四级手术,背后是家族请托与主任间的:
招呼。
招生、培养、学位授予、临床实践,环环失守。
王辰试图建立的精英教育新堡垒,最终没有抵挡住来自内部的、以裙带关系和特权思想为名的病毒的侵蚀。
4
如果说王辰的失败,是一次宏大改革遭遇现实引力的结构性溃败,那么另一位院长的风波,则揭示了另一种更微观、也更基础的病变,即科学诚信的动摇。
曹雪涛,是中国科学界一位履历耀眼的明星。
同样来自山东的他,1990年于第二军医大学直接获得博士学位,两年后即晋升为教授。
41岁时,他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他是一位极其高产的免疫学家,以通讯作者身份在《细胞》、《自然》、《科学》等国际顶级期刊发表论文超过:
230篇。
他的职业轨迹,从军医大学副校长,到中国医学科学院院长、北京协和医学院校长,再到南开大学校长,最终进入国家卫健委高层,成为一名:
副部级官员。
然而,在这条辉煌的晋升之路背后,却隐藏着巨大的争议。
2019年11月,国际学术监督网站PubPeer上,微生物学家伊丽莎白·比克(Elisabeth Bik)博士开始发布她的发现。

在曹雪涛作为通讯作者的论文中,存在大量实验图像不当使用的问题,例如流式细胞术图和蛋白质印迹图的复制和修改,被网友通俗地称为:
用PS代替做实验。
质疑如滚雪球般越滚越大,最终涉及的论文超过60篇,发表时间跨度长达15年以上,贯穿了他在不同机构任职的时期。
这起事件,成为中国现代科学史上最受关注的学术诚信调查之一。
当这场风暴将他置于聚光灯下,人们开始回溯他漫长的学术生涯,并发现了更多值得玩味的东西。
早在1989年,当他还是硕士研究生时,就曾与导师合著过一篇题为《气功外气的抗肿瘤作用及增强免疫功能机理的实验研究》的论文。
该文发表于《自然杂志》,声称:
气功师发放的外气能够抑制小鼠肿瘤生长。
这篇论文需要被置于其特定的历史背景中理解。

上世纪80年代是中国 气功热的顶峰,当时社会各界乃至部分科学界人士都对人体科学抱有极大热情和探索兴趣。
这篇早期的论文,与其说是他个人的学术污点,不如说是一个时代特殊思潮在他身上留下的深刻印记。
它与40年后那些被质疑用PS修改的、发表在国际顶刊上的精密图谱,共同构成了他科研生涯中两个意味深长的细节。
2021年1月,由科技部、教育部等多部门组成的联合工作机制公布了调查结论。

结论的措辞经过了精心的校准,未发现造假、剽窃和抄袭,但明确认定图片误用的问题确实存在,反映出:
实验室管理不严谨。
这是一个精确的官方定性。 它将持续多年的、系统性的学术不规范问题,定义为一种管理层面的疏忽。
曹雪涛因此事受到了实质性处罚。
除了在工程院内部进行通报批评之外,还被取消申报国家科技计划项目资格、取消作为财政资金支持的科技活动评审专家资格、取消招收研究生资格。处罚期均只有:
1年。
处罚期满后,他的仕途并未受阻。
这起事件标志着一种范式的转移。
在以项目、资金和论文产出为核心指标的大科学时代,产出的规模与速度,似乎拥有了比过程的绝对严谨更重的分量。
协和赖以立身的严谨学风,在新的评价体系压力下,显得如此脆弱。
5
回顾协和一个多世纪的领导史,一条清晰的轨迹浮现出来。
以顾方舟、黄家驷为代表的上一个世纪,协和的敌人是清晰的、外部的,是肆虐的病毒,是动荡的政治风暴。
他们的行为逻辑,是直面危机,解决问题。
进入21世纪,以王辰、曹雪涛为代表的新一代领导者,他们自身就是:
国家科技官僚体系的精英。
他们履历光鲜,手握重权,试图用更宏大的改革、更高效的科研产出来延续协和的辉煌。
然而,他们所要面对的敌人,却变得模糊、暧昧,且来自内部。
这些敌人,是裙带关系对程序正义的渗透,是学术KPI压力下对科研诚信的漠视,是整个社会日益功利化的风气对医学精神的侵蚀。
这是一种系统性的不适应症。
旧时代的道德武器似乎无法有效应对这些新的病症。 因为这些病症并非源自个体的沉沦,而是从滋生它们的土壤中蔓延开来。
宏大的改革蓝图,最终沦为特权的通道;惊人的论文产出,其根基却被发现并不坚实。
2025年8月,局外人吉训明院士的 到来, 外界的目光复杂而审慎。
这究竟是一次刮骨疗毒的开始,还仅仅是又一轮人事更迭的序曲?
他接手的,是一个荣誉与病症并存的复杂躯体。
作为新院长,他面临的挑战,不再是如何研制一枚糖丸或保住一个学制。
他的任务更为艰巨。
如何修补那些在21世纪的压力下被彻底暴露出来的结构性漏洞,并重建一个能有效抵御功利主义侵蚀的内部秩序。
这恐怕不是一个新院长能解决的问题。
文|孟妮卡
图片|收集自网络
封面图|电影《千与千寻》
驰盈配资-驰盈配资官网-网上配资门户-股票配资哪提示:文章来自网络,不代表本站观点。
- 上一篇:股票配资真平台但是当面对其他教师批评学生时
- 下一篇:没有了